上接:从女性视角看东大异变(上)——性别失衡与中国留学生激增的双重冲击

笔者陈小牧(中) 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与张春杰(右)、田思俭(左)交流
【人物介绍】
陈小牧:本次对谈主持人,日本留学问题专家。留日教育学硕士,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国费奖学金获得者,主要著书《日本留学之味》(日本名校50学子访谈录)。
张春杰:地球探测信息技术专业,本硕博毕业于中国高校,2022-2023年为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2025年起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在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从事人工智能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研究。
田思俭:土木工程专业,湖南大学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建筑学硕士,现于东京大学社会基盘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城市信息系统与人流模拟。
语言的混搭:博士教育中的国际化挑战
陈小牧:日本大学的国际化改革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然而在过去的 30 年里,日本大学与欧美顶尖高校的差距并未缩小,与此同时,亚洲邻国如韩国、中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迅速崛起,与日本大学的差距逐渐缩小。2013 年,日本曾提出“十年内十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 TOP100”的目标,但目前只有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进入榜单。尤其是日本的国立大学体系,因历史沿袭、体制复杂,国际化改革步履维艰。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日本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严格意义上不能完全对应“university”这个概念,因为缺少校长负责制等现代大学的核心机制。这也是其国际化排名落后的原因之一。那么,在博士课程中,日本的国际化程度如何?尤其是语言环境、课程设置方面,有哪些值得讨论的?
张春杰:理工科的国际化程度这几年确实提升了不少。课程很多用英文授课,实验室日常交流,尤其在国际化团队中,也多用英文。但问题在于,行政文件、教务系统、甚至学术汇报,有时仍要求日语。这就导致一种“混搭”状态:上课、写报告用英文,提交文件、参加会议却要用日语,对外国留学生是很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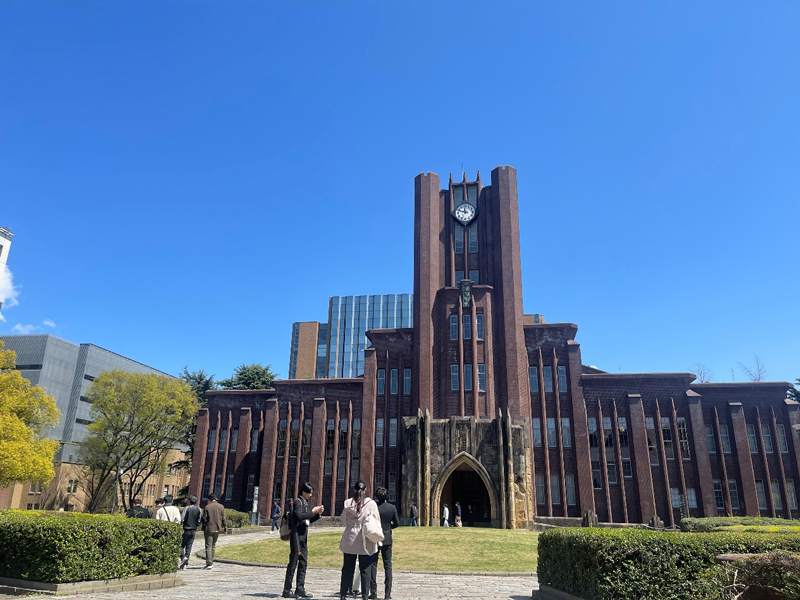
东京大学本乡校区安田讲堂
田思俭:完全同意。即使课程使用英文授课,某些教授的英文水平有限,讲解模糊不清,让学生听得一头雾水。我甚至遇到过放映的 PPT 是英文、授课全日语、最后考试写英文报告的情况……这种多语混杂状态对非日语母语者非常耗神。文科就更困难,大部分的课程、论文、文献都是日文。如果日语不过关,在我看来几乎无法融入学术圈。特别是准备论文答辩,全程日语,对一些外国留学生来说用日语表达复杂概念非常吃力,这实际上抬高了文科博士的门槛。
张春杰:对我个人来说,语言环境对研究的影响不大。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会日语后,日本人对你的要求会提高,他们会觉得你“进入了他们的文化圈”,希望你像他们一样。反而只用英语交流时,他们会更宽容,有时用英文反而更轻松自在。
田思俭:课程语言的影响其实有限,尤其博士阶段很多核心知识靠自学。但在本科阶段,有些学校提供全英文课程有限,只能播放录播视频,甚至有些根本开不出某门重要的基础课程,主要因为缺少能用英文授课的老师。幸运的是,我们系的老师大多可以用英文讲课,每周系内讨论和组会也是全英文。
陈小牧:当然,大学国际化并非只是单纯的语言英语化。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大学也有各种苦衷。我听说一些名校处理得挺灵活。有的外国留学生本科用英语学,研究生继续英文项目,但日本教授觉得留学生经过四年在日本的锤炼,日语原则上应该没问题,就默默切回日语授课。毕竟用母语讲课对教授来说更顺手。
田思俭:是的,我也见过。有些老师一开始用英文,讲着讲着就切换成日语,特别是在讲解复杂概念时,日语水平一般的外国留学生很容易掉队,只能放弃听讲。这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障碍。
陈小牧:之前我去庆应大学访问,接触过几位从海外留学回来的老师。他们英语非常好。有个中国本科留学生跟我说,一位从德国回来的教授,经常直接用英语“PUA”日本学生:“你们英语这么差还好意思睡觉!”但对国际学生却格外客气(笑)。
田思俭:日本社会极度讲究上下尊卑,尤其是日语的敬语系统,复杂到说话时需要小心翼翼,还得体现情绪色彩(気持ち)。用英语交流时,这些层次感消解了,表达反而直接清晰。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领域几乎全用英语研究和发表,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
张春杰:其实,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说,无论是日语还是英语,都是外语。某种程度上,这种语言隔阂反而带来“安全感”,让人更敢开口表达,也减少了社交焦虑。
东京的孤独与自由:秩序背后的冷漠
田思俭:东京生活虽然便利、安全,但社交生活非常贫乏。我经常感到一种“被系统规范性照顾却缺乏人情”的状态。比如学校事务处理高效,但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你的生活。这种“孤独感”对心理状态是一个考验。

田思俭在镰仓江之岛
张春杰:我也有类似的感受。日本的生活井然有序,但作为外国人,总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在研究室和日常生活中,总觉得自己是“被允许存在的客人”,而不是系统中真正的一部分。不过我也觉得,日本生活的“自由度”很高。没人管你几点睡、几点起,研究做得好不好也没人逼你。听起来很好,但这种放任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去责任化”——一切后果都要自己承担。博士阶段如果没有清晰的目标,很容易被边缘化。
日本大学的科研生态:奖励不足与“躺平”现象
张春杰:日本博士学习阶段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科研产出周期太长。相比欧美博士毕业时通常能拿出多篇论文,日本博士三到五年可能只有一到两篇文章,效率明显偏低。这并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卷”的学术文化。
当然,这和评价体系有关。日本更强调研究质量而非数量,但在国内的考核标准下,仅靠质量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未来要回中国发展的学生来说,就必须学会“卷”。除非能完全自洽,否则现实中很难两全。
田思俭:我很认同。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只是学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思考这个环境是否有助于未来发展。很多时候,研究者投入大量心力,却缺乏相应的奖励机制,这很容易消磨斗志。如果看不到努力的成果,创新动力自然下降。制度越僵化,创新空间就越小。
张春杰:尤其在职称晋升上,日本的年功序列非常严重。上面的人不退休,下面的人几乎没机会升迁。无论你多优秀,都得按年资熬,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社会被程序化,人就像齿轮被“嵌”进系统,很难突破。
陈小牧:日本也有它的道理:城市空间狭小,人口密度高,资源有限,没有秩序就会混乱。但这种体制对外国人来说,往往会感到拘谨和不适。
国际化的障碍:制度僵化与人才流失
陈小牧:除了学术环境,日本的社会支持系统却远远滞后。我一直认为,日本政府和大学表面上倡导国际化,试图突破日语壁垒、引入更多外国留学生,但如今随着外国人数量创新高,社会对留学生的友好度反而有所下降。比如,许多中国留学生来日本后想办理银行卡,却被要求必须在日满半年才允许。疫情期间,不少学生已在各自国内上了半年网课,并缴清学费,但入境日本后,银行却以“未满半年”为由多次拒绝办理。此外,对于选择英文授课的学生,许多银行仍坚持要求用日语面试,不接受英语。许多刚到日本、日语尚不流利的外国留学生到银行询问是否有英文服务时,往往得到的回答很决绝:没有。上述现象并非个案,留学生意见很大,也确实令一些有志来日本深造的顶尖人才感到失望,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转而选择前往欧美深造。
田思俭:这真的匪夷所思。学生已经注册、缴费,却被银行拒绝办卡,这就是不作为了。
陈小牧:我 90 年代末在日本留学时,办卡、办签证手续都简单得多。现在一方面是外国人自身存在不规范行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日本金融系统的过度保守。但这样的僵化环境,对刚到日本的人来说,无疑是困扰和打击。
张春杰:归根结底,就是缺少弹性。日本太依赖规则,把人固定死。对于需要灵活、鼓励创新的年轻学者,这种环境特别压抑。
创新与自由:科研生态的两面性
陈小牧:一个人是否进取,取决于内驱力和外驱力。日本的问题在于外部激励太少。人需要反馈:投入有产出,产出有奖励。完全靠自律是不现实的。职业运动员能坚持训练,是因为有比赛目标;如果只是自己在家练,估计多数人很快就放弃了。
张春杰:还是科研奖励机制出了问题。奖池里没有足够的“筹码”,外驱力不足,大家就不愿意拼精力去争。比如“破格”提拔,日本的“破格”太少了。太程序化,每个人都被“钉”在一个位置,按照规定的轨道转动,很难有真正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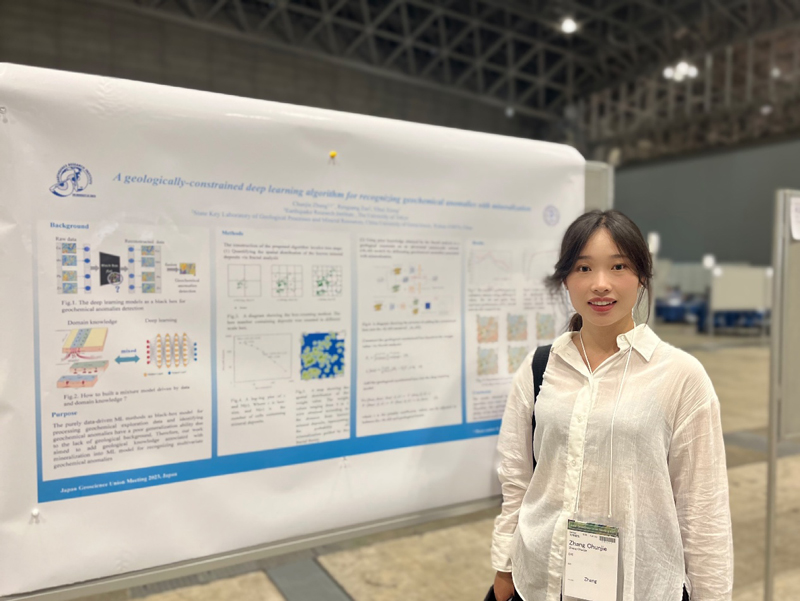
张春杰参加学术会议
田思俭:尤其是在没有惩罚、不设硬性 KPI 的环境里,竞争氛围被削弱。大家都知道不努力也没啥坏的后果,自然就不拼了。
陈小牧:说到底,这是结构性问题。比如秉议制、“村文化”(枪打出头鸟),仍在日本起着很大作用。日本学者自己也分析过,日本大学大致分三类人:改革派、保守派,最多的则是“躺平派”。
张春杰:在包括大学在内的日本研究机构,确实有一些教授多年没发表论文,本人也不急着晋升。比如我认识一位日本大学副教授,十年了,最近一篇论文还是 2019 年的。我常常好奇,他这些年到底在忙什么?感觉完全缺乏写论文的动力。
田思俭:我熟知的一位日本老师,2009 年前发表了很多好文章,但后来几乎停了。听说是当年投了一篇他自认为颠覆性的成果,结果被拒,之后就一蹶不振了,甚至一度放弃研究。虽然这没有影响他的职位和工资,但对他的打击很大,从此几乎不再发文。
张春杰:大学系统就像一排座位,坐在上面的上一代不退位,下一代就没机会。职位数量有限,让年轻人无法施展才华。
田思俭: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日本的科研生态。这里给了研究者自由探索的空间,这对创新很重要。你不需要完成 KPI,你可以专注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张春杰:没错。自由有助于探索,但如果想回中国发展,就要适应另一套考核体系。
田思俭:所以平衡特别重要。我的导师一方面关注主流研究方向,积极参与竞争,另一方面也鼓励学生探索非主流领域,双轨并行。
陈小牧:确实,有些日本学者一辈子研究厕所零件、电饭煲盖锁,这也是科研多样性的体现。但如果想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光靠“小而散”的项目恐怕是不够的。
国家竞争力的考验:自由与效率的拉锯战
陈小牧:从国家层面看,比如在 AI、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日本如果想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仅靠自由探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制度引导和外部激励。
田思俭:我有朋友曾在国内大厂工作了几年,后来辞职,说是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让人喘不过气。但也正是这种高度竞争,让国内在很多前沿领域进步飞快。
张春杰:我认识一位回国的青年教授,30 岁就拿到终身教职,但他常常焦虑,因为国内所有人都在拼命工作,他稍微放松一下就有强烈的内疚感。
陈小牧:国内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每年都有“成果展”“年终总结”,一年没产出甚至会被扣绩效。上台述职时,如果交不出成果,就是“社死”现场。哪怕家庭条件再好、经济无忧,也难完全摆脱社会评价和同侪(tóng chái)压力。
张春杰:日本这边给了你自由,但少了驱动力;中国那边压力大,却能快速推进。自由和效率,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田思俭:自由和效率之间确实是一对矛盾,需要找到平衡。松散的体制固然难以整体驱动科研高效产出,但它包容多元探索,这样的生态某种程度上其实非常珍贵。
陈小牧:无论是东大的性别比例、国际化改革,还是科研生态和青年学者的处境,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校内议题,而是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在全球化时代必须面对的挑战。自由与竞争、传统与革新、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拉扯,才是当下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供稿:陈小牧
图片:陈小牧、张春杰、田思俭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